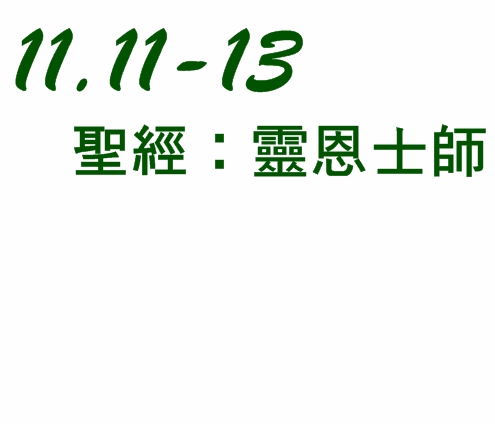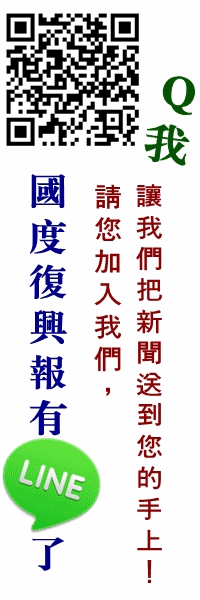文◎潘榮隆牧師
「哥,你是博士,說的一定是對的...。」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耳聾的,還是可以聽到另一種聲音。
「哥,你在跟我講話嗎?」么弟轉過頭來問我──我已經大聲喊了他三次。
么弟在我們兄弟中受的教育最少,說起話來有點粗魯,不像我們潘家其他人;他的急性子,可又是我們兄弟典型的特徵。他的個性怯懦軟弱,應該跟他排行老么、小時候常黏在父親身邊,受家人過度照顧有關。
「可能因為沒有當過兵吧。」二弟搶著解釋么弟懦弱的個性。「為什麼你不用當兵呢?」我問么弟。
「被刷下來──我左耳重聽。」么弟尷尬的回答。
驀然,我心頭一震。
我們家族並沒有耳疾的遺傳;我知道他為何重聽──我曾重重的甩過他一記耳光。
那一年,我在台大唸書,周圍有許多同學的家世很不錯,在他們的談話中,掛在嘴邊的常是,「姊姊(哥哥)在美國…」、「我妹妹在北一女…」、「我弟弟在建中…」。我很羨慕他們;我和他們的聊天,經常至此,我就語塞了。每當這時,我回頭一看自己的家庭,便常自慚形愧、自覺矮人一截,我的弟弟妹妹們可沒有一個肯用功唸書的啊。么弟更是如此,成天躲在家父身後,貪玩之餘無所事事,每次我看到他,總是氣憤難奈。
一個傍晚,我看到他趴在地上玩彈珠,「是什麼年紀了,書不唸,還迷這玩意兒。」我實在氣不過,就順手將彈珠一把給抓了起來,往窗外一扔,讓他再也不容易將它們找回來。
么弟滿臉驚愕,不知何從,爬了起來,諾諾的站在我面前,我就重重的給他甩了一個耳光。立即,只看到他手扶著左耳,彎著腰哀痛起來。我仍氣在心頭,不加理會,逕自忿忿地走開,二話不說地就背著行囊回台大宿舍去,留他一個人在那裡哭將起來。
我告訴自己,從今起再也不管他,當作沒有這麼個弟弟。
從此,我也就不太常回家,一股兒閉鎖自己在學校宿舍裡。
隨著大學畢業、金門當兵、出國留學,我和家人的關係若即若離。在美國念書時,更因文化語言差異的震盪,加上課業研究繁忙,自顧不暇,我們兄弟間好似斷了線的風箏,隨風飄去。在那樣的孤獨裡,有時看到同學們全家在美國「團圓」,竟有些吃味。而從前那些種種不滿,也就逐年消逝;代之的,反倒是一份濃濃親情的記憶,在我夢裡夜夜上演著──我何等的想念家人啊;甚至有時醒來,已經是淚濕了睡枕呢。
拿到學位後,我生了一場大病,孤單一人在異域,我惶恐不安至極。在病榻,我想的竟然不是自己的病況,是遠方的家人啊;而么弟的那事件,成了我的夢魘。
牧師的禱告、基督徒的安慰,在我無望之時,成為我的支柱,那不治之症也居然因此不藥而癒──我相信是神醫治了我。重生之後,我一心想望的,便是要把這大好信息與家人分享。不久,我便束裝回國,而家人的信主,也就成為我一生的負擔與使命。
「一定是當年我打了你一個耳光,使你患了重聽。」我帶著愧疚的口吻懺悔地說;我告訴他那件往事。
「有這回事嗎?…我不記得了耶。」么弟摸摸左耳,不解的說,「哥哥,你一直都很愛我們啊。」
我多麼希望他對我生氣,數落我當年的不是,罵罵我那時的凶狠。至少我可以有機會認罪、求饒恕、得釋放啊;何況,作為一個基督徒,我可是很會認罪的哦。
「還好,只是重聽,沒有什麼影響。」么弟笑笑地說,「我的乘客都坐在我右邊,我聽得到他們說要去的地點。」──他沒有唸過多少書,只能當個計程車運將。
我跟他說了我的醫治與改變。末了,我問他願意不願意也信耶穌。
「我願意。」么弟說,「哥,你是博士,說的一定是對的。」
我的眼淚竟然不聽使喚的奪眶而出。
從前我叫他唸書,都叫不動,他那時好像是一個重聽的人。今天我才開口問他要不要信耶穌,他便一口氣答應了。我知道他現在真的是一個耳朵有毛病、重聽的人,我說的話他應該沒聽進去。但他就是這樣信了耶穌;這樣的神蹟,一定不是聽了我說的話,──他一定是聽到了神在呼喚他。
哪怕是耳聾的,一定還是可以聽到神的聲音──我深深相信。那一天,么弟的耳朵雖然還是沒得醫治,他卻已經可以聽見神對他說的話,而我那時,才真正得釋放呢。
Loading